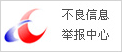二哥
二哥走后第七天,我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鸟,飞过我们曾一起收获过油菜籽的山梁,却怎么也找不到他曾经咆哮过的那个弯——是不是连土地也学会了沉默。
七天前,我握着手机,听筒里传来的乡音像从一口很深很深的井底浮上来的,字字却像生锈的钉子,狠狠凿进耳膜:“……二哥,今早五时,走了。”走了。这两个字轻飘飘的,落下来却像一座山,压得胸腔里那点热气倏地散了。今年春节大年初一,二哥还和一大家子人在我家吃饭,怎么一转眼,人就成“故人”了?我一下子瘫坐在椅子里,不能自已。回忆像破了堤的洪水,不管不顾地冲撞上来。
最先涌来的,竟是他的咆哮。那一年农忙时节抢收油菜籽,那时的山地,田是挂在坡上的,路是盘在山腰的“肠子”。满满当当的一板车的油菜籽秆,黄澄澄的,像是汗水泡出来的希望。山路崎岖,人疲马乏。不知是谁手滑了一下,也许是车辙碾到路边一块松动的石头,只听得“哗啦”一声响,车翻了,油菜籽杆撒了一地,有些油菜籽从壳里蹦了出来,混进泥土、碎石、青草里,黑油油一大片,在正午毒辣的阳光里,显得格外扎眼。二哥就那样站着,脖子上的青筋蚯蚓般暴起,脸膛由红转紫,对着苍茫茫的天,对着沉默的山,发出一种近乎兽般的、绝望而又不屈的咆哮。那声音里没有具体的词句,只有最原始的痛惜、劳累、焦灼,还有一种被老天爷戏弄后不肯低头的愤懑。我们大气不敢出一声,只是埋下头,用最快的速度,近乎虔诚地,将一根根油茶籽杆重新码在车上。没有人说话,只有粗重的喘息和油菜籽秆摩擦车栏杆的嚓嚓声。收拾完了,他吐一口唾沫,闷声不响地扶正板车,套上肩绳,脖颈再次深深埋下,拉车继续前行。那背影,像一张拉满了却不肯松弦的弓。
可这样的咆哮,在他一生中是罕有的。更多时候的二哥是沉默的,对谁都陪着小心,笑容是收敛的,说话是斟酌的,那是一种长期处于无根无底、家无余财的境况里浸润出的、农民式的谨慎与谦卑。我更难忘的是他的一种笑,那是举杯庆丰收时,从胸腔里震荡出来的、爽朗的,甚至有些傻气的大笑。那是在大年三十吃团圆饭时,一大家子人围坐在一起,两瓶酒,几样粗粝但实在的年菜。酒过几巡,他的话会多起来,脸上放出光。他说起了在邻村日升大队跟我父亲一起挖莲藕的事。
“嘿,那个冷,才叫真的冷!那个冻,才叫真的冻!”他比划着,“脱了鞋,赤脚往那泥塘里一踩——嗬!”他猛地倒吸一口凉气,仿佛那股寒气此刻还钻在脚底板,“像是千万根针在扎,‘嗖’一下,从脚心直蹿到天灵盖!整个脚,一下子就不是自己的了,木了,没知觉了!”他端起小碗,狠狠灌了一大口,辣得眯起眼,咂咂嘴,那被生活磨砺得粗粝的脸上,却泛起一层奇异的光泽,混合着对往日艰辛的回味与战胜它的得意。“得咬着牙,在里面豁命地动,挖!慢慢地,哎,那股麻劲过去,血好像才又活过来……”他看向我父亲,眼神亮晶晶的,“爹,你说是不是?那活儿,苦是真苦,冻是真冻。可值啊!不然,像今年这天干的,塘都见了底,过年哪来这藕片炖肉?哪能坐在这儿,安安稳稳过个像样的年?”他嘿嘿地笑,那笑声里有种朴素的、沉甸甸的满足,一种用最原始的力气与忍耐,从老天爷指缝里抠出一点甜头来的、农民式的小得意。
那氛围,是冷的极致与暖的极致交织成的,是年味里最厚实、最让人心安的一部分。我常年漂泊在外,离家千里,有了二哥和亲戚们照顾父母,我心里才像有了一块压舱石。每次春节回家,我握着他那双骨节粗大、布满裂口和老茧的手,心里总翻涌着说不清的愧欠。他总是不等我说完,就用力摆摆手,声音不高,却斩钉截铁:“一家人,不说两家话。爹就是爹,照顾他,还不是应该的?”我记得有一次过年在他家吃饭,他总是给我夹菜,自己碗里的饭却半天不见少。我劝他多吃点,他咧嘴一笑:“我吃得少,习惯了。一天也动不了多少脑子,吃多了胀得慌。”可他每天干的,是比脑力繁重百倍的体力活。他一直很瘦,瘦得颧骨突出,手臂上几乎没什么肉,青筋蜿蜒在古铜色的皮肤下。我记忆里的二哥,仿佛从来就是这个清瘦的模样。也许他一生,都未曾真正“胖”过。那是一种被生活本身,被日复一日的劳作与清贫,精细地、缓慢地“雕刻”出的瘦,瘦得筋骨分明,瘦得像那山间扎根的老松。
今年春节见他时,我看到他气色还不错。谁能想到,仅仅几个月后,就传来他病重的消息。我母亲在电话里说,二哥去医院看了病,医生没让住院,只开了些药,让回家“好好休息”。又过些日子,说他吃不进饭了,人瘦得脱了形。再然后……就是这通电话,把“走了”两个字,像讣告的印章,冰冷地盖在了他六十年的人生上。
回忆及此,泪水不知何时爬了满脸,冰凉地划过嘴角,带着咸涩的滋味。我只能对着这无边的、千里之外的夜,喃喃自语,像寄出一封无处投递的信:二哥,你去的地方,一定没有苦痛了吧?一定不用再顶着毒日头,或是咬着牙踩进冰碴子里,去劳作吧?你应该能和早走的三哥、大伯、爷爷、奶奶团聚了吧?到了那儿,活儿,总该轻省些了吧?我多想,多想看看你啊,看看你脸上长了些肉,身子变得圆润,笑起来眼角的褶子都舒展开,变成一个我从未见过的、白白胖胖的二哥……
夜色苍茫,无边的黑暗仿佛吸走了所有的声音,我只听到心口处,一阵阵空洞的、钝钝的回响。是这家乡的山太重,回乡的路太长,甚至连梦,都显得太轻,太薄,载不动这一生的泥土与风霜。睡梦中,我似乎变成了一只倦鸟,奋力扑打着翅膀,飞越千山,飞到那我们曾用脚步丈量过无数次的、熟悉的山梁。长风在耳边呼啸,我急切地寻找着,寻找那个二哥曾对着苍天怒吼过的急弯。下方,田野沉默,山峦沉默,连曾经撒过油菜籽的那片泥土,也只剩下一片被夜色浸透的、无言的深褐。什么都没有了,似乎连土地也学会了二哥的沉默。
作者:张涛
热点图片
- 头条新闻
- 新闻推荐
最新专题

- 五度春秋笃行不怠,奋斗历程波澜壮阔。十四五时期,龙川县深入贯彻落实省委、市委决策部署,牢牢把握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,统筹高质量发展与安全,推动县域经济稳健前行,产业结构持续升级,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