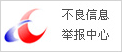一张老式三屉桌
故乡的老屋要拆,很多旧物都被淘汰了,我却执意要留下那张老式三屉桌。妹妹说:“新房子盖起来,家具都要换新的,这东西放哪儿呢?”
妹妹比我小八岁,她对这张老式三屉桌的感情远不如我。世间所有的感情,都是一日日叠加出来的。这张三屉桌,妹妹用得不多,所以她并不在意。可是对我来说,三屉桌就像陪我经风沐雨的患难之交,彼此血脉相连,难以割舍。
这张三屉桌是专门为我打的。我上初中后,总是在饭桌上写作业,一不小心书本就被油渍弄脏了。我是极爱书的人,为此恼恨不已,吵着要一张书桌。父亲决定打一张三屉桌,为了充分利用三屉桌,他计划打三屉两柜的样式。我利用桌面写作业,抽屉和柜子可以存放家里的物品。
父亲刨了院子里的一棵槐树,用来做三屉桌。村里木工活最好的是村南的刘叔,不过他很难请。父亲费了好大的劲,才把刘叔请来。那时给人做木工活不给工钱,好菜好饭招待就行。母亲把家里最好的食材拿出来,给刘叔做最丰盛的午饭。那几天,院子里总是飘着浓浓的炒鸡蛋和煎腊肉的香味。除此之外,还有淡淡的木香。刘叔坐在木材中间,量、锯、刨,胸有成竹地忙碌着。他动作从容舒展,显出游刃有余的气度。他从容的样子,让我佩服。有时我会搬个小马扎,看着刨花飞扬中的刘叔,一看就是小半天。
三屉桌的雏形出来了,比一般人家的三屉桌要矮一点,因为我要在上面写作业,所以是按照我的需求设计的。父亲私下说:“大刘的手艺绝对是咱村第一,瞧这三屉桌,做得严丝合缝!”母亲对刘叔的手艺也很满意,她说:“夸人的话,当着人家的面说比较好。”母亲当着刘叔的面,把他的手艺狠狠夸了一通。刘叔得意极了,准备来个“炫技之作”:他想把三屉桌前面的两个角打个花样出来,我们当然乐意。
三屉桌打好了,效果极好。光洁美观,简单大方,还透着手艺人打磨出来的灵气。三屉桌放到屋子里,真有蓬荜生辉的效果。三屉桌下面虽然有两个柜子,但给我的腿留出了地方。我坐在桌前写作业,可以把腿伸展开。这样的设计,在当时还是蛮有创意的。我非常喜欢这张三屉桌,每天都会把它擦得一尘不染。后来我跟母亲提要求,希望有一个专属于我的抽屉,母亲答应了。三屉桌最右边的抽屉是我的,开始写日记以后,我每天都把抽屉锁好。小锁的开合之间,我与三屉桌也在交流心事与秘密。那时我以为所谓的相濡以沫,就是这样的关系:彼此陪伴,彼此懂得,彼此取暖。
后来妹妹也上学了,她也在三屉桌一角写作业。她从记事起就觉得,三屉桌是我的,她只是借用我的地盘。有时母亲找东西,妹妹会说:“在我姐的三屉桌上。”可让我没想到的是,有一次她竟然反客为主,偷偷在我的三屉桌上刻了个“早”字。我气得揍了她一顿,她哭着说:“我写作业的时候,忘了是在家里,还以为在学校呢,同学们都在课桌上刻早字。”她指天发誓,以后再也不会祸害我的三屉桌。我摸着她的头,原谅了她。
可是,时间的刻刀却不停地在三屉桌上留下痕迹。三屉桌慢慢变得苍老,上面的痕迹越来越多,仿佛人在岁月流逝中长出的皱纹。多年后,三屉桌呈现出垂垂老矣的姿态,但这并不妨碍我对它的感情。
有一天我读到一首小诗:“做一张桌子,需要木头;要有木头,需要大树;要有大树,需要种子;要有种子,需要果实;要有果实,需要花朵。做一张桌子,需要一朵花。”我觉得这首诗特别有韵味。我家的这张三屉桌,所有的履历都如花开般诗意美好:它从一朵槐花开始,慢慢变成种子,种子发芽后成为小树苗,小树苗长成参天大树,刨掉大树成为木材;最重要的是,它被人带着美好的情怀做成桌子,然后被我珍爱使用了很多年。漫长的岁月中,它最后也老成了一朵花。
作者:马亚伟
热点图片
- 头条新闻
- 新闻推荐
最新专题

- 强国必先强教,强教必先强师。今年9月10日是我国第41个教师节,主题是“以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,谱写教育强国建设华章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