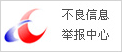种春天的人
那个总爱穿褪色蓝布衫的女人,是我小学四年级的班主任。她姓陈,手指关节处常沾着粉笔灰,像星星碎屑嵌在皱纹里。
那时我们村小只有三间土坯房,漏雨的屋檐下摆着用砖头垫高的长凳,她每天清晨第一个到校,用搪瓷盆接住瓦缝滴下的水,再踮脚把歪斜的课桌摆正。有次暴雨冲垮了教室后墙,她带着我们搬来装化肥的塑料袋糊窗户,塑料布在风里哗啦啦响,她笑着说是大自然在给我们伴奏。
她教语文时总把课本卷成筒状,讲到激动处就用卷筒轻敲自己太阳穴。有篇课文描写火烧云,她突然扔下粉笔冲出门,回来时发梢沾着露水,从衣兜里掏出半块烧饼:快看!云彩把烧饼染红了!后来我才知道,她饿着肚子跑了三里地,就为给我们找块带焦糖色的烧饼当教具。最难忘的是她批改作文的方式——不用红笔打叉,只在错字旁画个小问号,本子边缘却总粘着晒干的野花,那是她家后院种的指甲花,她说错误和鲜花都是成长的印记。
记得有个总尿裤子的男孩,她从不嫌弃,只是默默在讲台旁放个陶罐。有次男孩又尿湿了棉裤,她把自己织的毛线裤裹在孩子身上,陶罐里立刻响起哗啦啦的水声。我们哄笑起来,她却严肃地摇头:“听见了吗?这是黄河在唱歌。”后来她每天给男孩带个煮鸡蛋,直到他不再需要陶罐伴奏。还有个女孩总偷拿同学橡皮,她没当众揭穿,只是把橡皮雕成小兔子模样:“看,它想跳回你铅笔盒睡觉呢。”女孩自觉不对,遂改了这个不好的习惯。老师第二天带来了用野草莓串成的项链,那是她家篱笆上长的,酸得我们龇牙咧嘴,她照样戴在脖子上。
她改作业的煤油灯总亮到深夜,灯烟把她的脸熏得黢黑,像块被火烤过的地瓜。有次有人半夜起来上厕所,看见窗纸上晃动着她的影子。她正用冻僵的手指翻作业本,嘴里含着热毛巾取暖。后来我们才知道,她得了严重的关节炎。第二天她依然准时敲响铁皮铃,只是走路时总扶着墙,粉笔灰簌簌落在她磨破的布鞋上。同学们凑钱给她买护膝,她转手就钉在教室漏风的窗户上,说:“这是会笑的窗花。”
毕业前春游,陈老师带我们去后山采野花。她教我们把蒲公英编成皇冠,用狗尾巴草做戒指。突然下雨,大家挤在破庙里,她变戏法似的掏出个铁皮盒,里面是晒干的橘皮和话梅核。我们嚼着酸涩的橘皮,听她讲每颗种子都能长成大树。雨停时,她蹲下身给每个孩子系鞋带,蓝布衫后背洇湿一片,像幅未完成的水墨画。后来才知道,她那天发着高烧,却把药钱换成了铁皮盒里的糖果。
最难忘的是她给辍学女孩补课的事。那女孩要照顾瘫痪的母亲,陈老师就每天放学后绕三里路去她家,在灶台边支起小木凳讲课。有次我去送作业本,看见她正用烧火棍在地上演算数学题。女孩母亲突然抽搐,她立刻蹲下身给这位母亲揉腿,转头她就对女孩说:“你看,这就像解一道人生的方程,你人生的答案就在这里。”后来女孩考上了师范,回校任教那天,陈老师把珍藏多年的红笔送给她,笔杆上还缠着当年灶台边用的草绳。
毕业那年,她送我们每人一包野花种子,说:“等你们长成大人,花儿就开了。”现在每当我看见指甲花,就会想起她发梢的粉笔灰,想起她讲火烧云时眼里的光。前年回村,听说她退休后还在扫校门口的落叶,巧合的是,她依然身着蓝布衫,被风鼓起时像面永远不会降下的旗。
作者:董国宾
上一篇:讲台边的旧时光(组诗)
下一篇:展卷又见老庄
热点图片
- 头条新闻
- 新闻推荐
最新专题

- 强国必先强教,强教必先强师。今年9月10日是我国第41个教师节,主题是“以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,谱写教育强国建设华章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