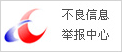雨的情怀
又下雨了。淅淅沥沥的雨声,勾起我童年的回忆,牵动我的心灵,细细地布满我的心底那纤细、柔软的感性神经,温馨、幸福的感觉便慢慢地、慢慢地溢满我的胸怀。
记得那还是大集体的时候,我那时刚四五岁的样子。爸爸因自幼体弱,无法胜任生产队的体力劳动,便出去外面做点小营生帮补家用。家中,只剩下妈妈和我们兄妹四个。兄妹们年幼,妈妈一个人的劳动力,在那时便显得异常薄弱。妈妈天天出工,待到结账时,年年都是超支。
有一件事,到如今我还记忆犹新。那年队里秋收后分粮,大家都欢欢喜喜地挑着黄澄澄、散发着阳光味道的稻谷往家走。妈妈也挑了一担大箩筐,领着我去生产队的大仓库里领粮。
仓库在晒谷场的边上,上去的时候要走一道土坡。我们上去的时候,地塘上面摆着一架风车,那时任生产队长的,是我的堂叔黑子。我们去时,他正将自己家分到的谷子倒进公家的风车里,然后一手摇动着风车把子,一手拿起脖子上挂着的那条白毛巾在擦汗。
“黑子,给我称粮。”妈妈喊着堂叔。堂叔瞄了妈妈一眼,说:“你超支,没有粮食分。”
“你就先给我分点吧,我们家都断粮好多天了。你的侄子侄女已经好几天都只吃番薯芋头了。你先给我预支点,明年在我的工分上扣除,好不好?”
堂叔面无表情,说了句:“就你这个劳动力,还想盈余?你年年都是超支的,多说无益,你还是快回去吧!”
妈妈低下头,缓缓地拿起系着两只空箩筐的扁担,搁在肩上,小声跟我说:“囡,走吧。”
从仓库到我们家,横穿着一条黄泥路。这条黄泥路,初建时挺好,平平整整的,赤着脚踩上去,温温润润,异常舒服。日子久了,风吹雨淋的,黄泥被冲走不少,路上便露出许多怪石来,插在土上,道路也变得异常坑洼难走。我很小心地走着,为免一个不小心,就被横在道路上的石子绊倒,摔到路两旁的水田里去。
是以,我便低着头,数着脚下的石子,小心翼翼地绕过去,不让它们有机会绊倒我。
妈妈跟在我背后,走得很慢,低着头一声不出。偶一回头,我看看妈妈正偷偷地用袖子擦眼睛,而袖子上,沾满了她在黄昏时帮生产队在地塘里收稻谷时沾的稻谷毛。我被那毛沾过,那毛,一旦沾上皮肤,便红肿,又痛又痒。妈妈浑然不觉那些沾人的谷毛已经布满了脸庞,只是眼睛,不知道是因为悲伤还是谷毛的侵害,变得红红的。
数天后,爸爸回到了家中,我听到他们在低声商量着,要拿钱去买高价粮来渡难关。那时候,莫说你没钱,就是有钱,没有票也是很难买到粮食的。
妈妈是个坚强的人。自打那天起,就更加努力地劳作着。
我常常早上睡醒起来,妈妈已在灶膛的大锅里煮好了清可照镜的粥水,大铁锅里煮好了半锅自家自留地里种的番薯。而妈妈,在这个时候,多担着一担刚从山上割下来的还沾着露水的“路基”(一种山上长的野草,晒干后可燃),放在家门口的泥地上,一边解开绳子铺晒,一边柔声叫着我:“囡儿,饿了去吃番薯哦。”
那时候,别人家的番薯都种得极小极精致,唯独我们家的番薯,是又大又香,只是番薯上面经常长满了虫子,那些虫叫钻心虫,一旦钻进番薯里,那番薯便会变得苦涩难吃。而那些极小极精致的番薯,看上去却是光溜溜的,极致可爱,吃的时候,也是满口余香。我就吵着要吃那种极小极精致的番薯,但是妈妈跟我说,那种极小极精致的番薯,是白着土种的,啥肥都不施,产量极低。而这些极大极香,但时常有虫子的番薯,则是妈妈在种的时候将家里路基烧成的灰,混了尿水挑了去,埋下薯苗,盖上肥料,覆上土,再在泥土上面盖上一层稻草种出来。这种方法种出来的番薯产量极大。哥哥总是笑着跟我说: “小妹,妈妈种的番薯一条就可以吃饱了。”那个时候,鲜少有香喷喷的米饭可以果腹,有的,都是些清稀的粥水和半铁锅的番薯芋头。
更多时候,妈妈还将家中吃不完的番薯切成条,晒干,没粮食的时候上锅蒸了,给我们吃。我们叫它 “番薯格”。再有时候,妈妈将番薯洗净上锅蒸熟,切成片,晒干。这种番薯在晒至半干的时候,非常好吃,软软的,糯糯的,咬一口,甜极了,而如果保存的时间久了,上面还会长一层白白的霜,那层白白的东西可不是霉粉,而是“上粉了”。“上了粉”的番薯干,是最甜最好吃的了。像这种晒半干的,妈妈就给我们当零食。它是我永不能忘的童年滋味,这种味道,陪伴着我的整个童年。而当这种番薯干晒到全干的时候,便会变得很硬,甜还是一样甜,就是咬一口,咯得牙齿生痛。这个时候,妈妈便拿水洗了,放在锅里回蒸,软了,便好吃了。而在过年的时候,爸爸带回油来,妈妈便拿它们放在油锅里炸,待炸成金黄色捞出。这个时候,你拿一片,放在嘴里一咬,一嚼,顿觉满颊生香。那脆脆的、酥酥的、香香的、甜甜的感觉,至今想起,仍让人垂涎欲滴。
“囡,跟妈妈去摘菜,我给你剥芥菜芯吃。”妈妈晒好路基,从柴房里挑出一担便桶,里面盛了尿,去河边将桶装满水,再挑着到我们家的菜园里。
妈妈总是将一天要吃的青菜摘出,然后再浇水。青菜隔五天浇一次尿水,平时早早晚晚都只浇清水。妈妈会绕着浇,要吃的菜在两个星期内都不会浇尿水的。妈妈的菜种得可好了,瓜果满园,吃不完的晒成干,乡亲邻里都来摘妈妈的菜,妈妈总笑着招呼:有,要就来摘哦。为此,妈妈很自豪,在多年后,都经常说:邻里乡亲哪个没有吃过我种的菜?
在河里洗完一家人的衣服,妈妈就要去上工了,大集体的年代,不去是没有工分的。哥哥姐姐都上学了,家里便只剩我一人。
妈妈去了上工,我就坐在大门的门墩上面,等着妈妈回来,等着等着,就睡着了。巴子叔叔回来,把我摇醒,说我妈妈叫他先回来看看我。巴子叔叔比我大十多岁,因为家里劳动力不足,早早地就跟着队里人上地挣工分了。叔叔人很好,说话风趣,总喜欢逗我,也经常帮着我家干点妈妈干不了的活。
“我妈妈呢?”我揉着惺忪的眼睛问他。我想妈妈了。
“你妈妈踩爆了队里的秤砣,被抓起来,回不来了。”叔叔逗我。
我“哇”地一声大哭起来,拉着叔叔的裤脚:“叔叔,你救救我妈妈,你去救我妈妈。”
叔叔哈哈大笑起来:“傻侄女,秤砣怎能踩得爆?你妈妈是趁下工时间去打理菜园去了。”
妈妈回来了,背回来一大捆番薯苗,招呼我跟她一块剁了,放锅里煮熟喂猪。那时候,家里喂条猪,到过年的时候给生产队杀了,是可以抵工分的。
妈妈告诉我,要等猪食晾凉才可以喂给猪吃,猪是急性子的动物,一看见食物就会迫不及待。猪食太烫,会烫伤食管的。
待猪食晾凉,哥哥姐姐们也都已经睡着了,他们明天还要上学呢。猪舍在房子的外面,黑,妈妈怕,就总是拉着我,掌着灯,提上猪食,让我在前面引路。在等猪吃食的时候,我总是靠着猪栏外面的木头睡着。
那时,我就天天盼着下雨。
下雨天,生产队不开工,妈妈也不能出去忙自家的活,她就能整天的在家里陪着我们。
下雨的时候,妈妈会给我们煮糯米饭吃,糯米先泡上几十分钟,在这其间将香芋削皮洗净切成2 厘米见方的块,在灶膛里生上火,铁锅里加上油、盐,将糯米跟香芋倒进锅里,加适量的水,盖上盖子慢慢地焖,在将好的时候洒上自家种的炒过的芝麻,再焖上一阵,那香喷喷的味道,瞬间便在屋里弥漫开来,配上滴滴答答雨打芭蕉的声音,实在是美妙极了。
如雨下得再大点,妈妈便会将家里辗米后从米糠里筛出来的米碎,叫上我跟姐姐,一起到下厅的石磨前,妈妈和姐姐推磨,我则将米碎少少地加在上磨的洞里。将米碎细细地磨了,再拿个粉筛一遍一遍地筛,筛出细细的粉末,拌上香葱、盐、芝麻,极细极细地揉了,做一锅香喷喷、软糯糯的糯米粄,让我们享用。
那个时候,我们一家人围在灶台边,一边烤火,一边听妈妈讲白雪公主,霍山的由来,田螺姑娘的故事。
妈妈的故事,伴着淅淅沥沥的雨声,像乐曲般美妙,似火光般温暖,更像小河的流水,轻柔、缓慢、绵长……
改革开放,大家不再吃大锅饭了。队里实行分田责任制,家里分到了属于自己的土地,人们改变传统种水稻的办法,不再自己留谷种,而是跟国家购买 “杂优”种子。我记得那时种的叫“汕优”。这种种子育出来的秧苗会自己分蘖,然后结出来的粮食也非常大串,谷子成熟时长长的,饱满极了。那一年,妈妈很高兴地宣布:我们家丰收了,一亩地收获了两千斤粮食呢。
大家不再挨饿了,清可鉴人的粥水已经一去不复返了。那些陪伴我成长的我吃腻了的“番薯格” 也只是偶尔地出现在饭桌上。我开始上学,放学回来,总能吃到妈妈煮好搁在锅里温着的饭菜,而勤劳的母亲,这时候不是在菜园就是在自家自留地里忙活着呢。
我还是很期盼下雨,下雨的时候,无论我何时回到家,妈妈总是在家里,给我们磨豆腐;为我们煮拌了猪油渣,加了炒芝麻,香香糯糯的糯米粄;一家人围着饭桌,玩猜字游戏;领着我们唱“东方红,太阳升……”
郑碧丽
相关阅读
热点图片
- 头条新闻
- 新闻推荐
最新专题

- 强国必先强教,强教必先强师。今年9月10日是我国第41个教师节,主题是“以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,谱写教育强国建设华章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