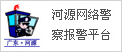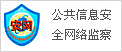母亲的小磨元宵
每到元宵节,我就会想念母亲的小磨元宵。
“磨磨磨,磨糯米,糯米粉儿白如雪。”母亲左手推着磨盘,右手投着料,嘴里哼着古老的歌谣。布满了岁月痕迹的小磨盘,没有倚老卖老,倒像个听话的孩子,跟随着母亲的手转动着,发出“吱呀吱呀”的撒娇声。磨盘上投料的小洞,又像孩子张开的小嘴,等待着母亲一勺一勺给它喂食。那洁白的糯米在石磨的碾压下,渐渐变成了细腻柔滑的粉末,从下盘边缘细细流出,透着一股米香。其实,我家那时还有盘大磨,可母亲却宁愿多花时间,独自磨上一上午,也不愿用那大磨。她说,用小磨一把一把磨出的糯米粉,做出来的元宵吃起来才香。
元宵的馅是猪板油和加糖的芝麻粉。猪板油是过年前就买好的,芝麻是家里秋天收下的。炒熟的黑芝麻油光发亮,被母亲用干瓢盛起倒到桌面上。然后,她握着枣木擀面杖,一下一下碾过去,芝麻向前滑动着,躲避着,但终究被压在了擀面杖下,发出了细碎的噼啪声,像是春冰初裂,又像是遥远的爆竹,继而声音变得绵密,芝麻在重压下绽开,渗出油脂,散发出温热的香气。慢慢地,它顺着擀面杖爬上来,缠绕着母亲的手腕,钻进袖口。母亲继续碾着,香气越发浓郁,在厨房里流动,漫过橱柜,爬上窗棂,最后从门缝里溢出去,飘向更远的地方。擀好后的芝麻面,母亲拌上红糠,盛了半小碗递给我。得了香甜的芝麻面,我得意地端着碗去找小伙伴显摆去了。
包元宵了,一家人围坐在小桌旁,桌上摆放着准备好的糯米粉和馅料。母亲揉好糯米粉团,熟练地揪下一小团,搓成圆球,用手轻轻一按,按出一个凹洞,放入馅料,然后慢慢收口,再一圈一圈地转动,一颗圆润小巧的元宵就诞生了。母亲边包边给姐姐哥哥们示范着:面团要捏成小碗状,馅料不能多也不能少,收口要像包包子一样打褶。打好褶再放在手中用两手搓圆。可糯米粉团似乎并不听他们的使唤,个个总是弄得满脸都是,你望望我,我看看你,发出了会心的笑。在欢声笑语中,一颗颗形态各异的元宵整齐地排列在盘子里,每一个都充满了童真和欢乐。
父亲已烧好一锅水,水在锅里欢快地沸腾着,就像我们此刻的心情一样热烈。母亲将包好的元宵小心翼翼地顺着锅边滑入锅中,白色的元宵在沸水中沉浮,渐渐变得透明,能看见里面黑亮的馅料。母亲用漏勺轻轻搅动,热气腾腾中,她的笑容格外温暖。
元宵煮好后,盛在碗里,冒着腾腾的热气。我总是抢着站到锅台边,第一个端过碗来,迫不及待地拿起筷子,夹起一个元宵,吹了吹,然后放入口中。那软糯的面皮包裹着香甜的馅料,在口中化开的瞬间,甜蜜的滋味立即充满了整个口腔,也填满了我的心。我吃得狼吞虎咽,连滚烫的感觉都没有察觉到,只是一个劲地享受着这美味。
如今,母亲走了十多年,老屋早没了踪影,那盘小石磨也不知落到了何方。可每年元宵节,我都会梦见母亲磨粉的身影,听见石磨“吱呀吱呀”的响声,闻到芝麻的香气,只是再也吃不到母亲的小磨元宵了。
现在的元宵节,我们年年仍旧吃元宵,但只能去超市买来现成的,虽然各种口味都有,可就是吃不出母亲的小磨元宵的味道。我终于明白,我们想吃的不是元宵,而是母亲的味道、母亲的爱。
作者:汪树明
热点图片
- 头条新闻
- 新闻推荐
最新专题

- 《河源市暴雨灾害预警与响应条例》被省人大作为全省高质量地方立法典型案例作重点推介;市人大代表履职案例《一件人大代表建议点燃一片人间烟火气》获评省人大常委会2024年度全省人大代表履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