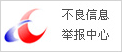“瓶装” 的童乐
幼年时,乡村孩童游戏娱乐的玩具,几乎没有从商店购来的,大抵是自制或就地取材,譬如跳房、攻城、打尺棍、滚铁环等,上了年纪的都知晓。
冬天过,春天来,白昼时光就像拉着的橡皮筋,逐渐升长。
下午,儿童归来散学早,用乡人的话说,时光还是“半下午”。那些小学堂的老师们,在黑板上耕耘完了,还要到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去耕耘,犁田耙地呢。
我们小孩儿好比无人看管的牛羊,散养在野外,自由自在,无拘无束,四处晃荡玩耍。
女娃子自会扎堆,咿咿呀呀唱着童谣,扭着腰肢,跳着皮筋或踢着毽子。男孩子却有自己的活动项目,掏蜂儿即是其中之一,来打发丰盈的时光。
春日,阳光黄金一样照在农家房屋的泥墙上。泥墙仿佛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,满脸沟壑纵横,阡陌交错,泛出黄白的肤色。
那些土蜂(相对会酿蜜的蜜蜂而言,称之为土)“嗡嗡嗡”,在土墙上钻进飞出。土墙上被无数土蜂挖满了鼻孔大小的洞。土墙像是位长满老年暗斑的老人,暗淡无光。
我们男孩右手拿着玻璃瓶,左手捏着一根从灶前柴窝里折来的蕨棍,全副武装,到泥墙上去掏土蜂。
那些玻璃瓶,不外乎吃水果罐头剩下的瓶子,一部分或是医院里打吊针扔掉的药瓶,再不济,最小的是青霉素的瓶子。它们都是小孩子看重的物品,只要能装东西就行。
“嗡嗡嗡”的家伙明明飞进洞里时,是头朝里尾朝外,怎么挖出来的时候,却是头朝外尾朝里?我们也懒得多想,只要用蕨棍,能把它们从洞里挖出来,便是我们的目标。
这些家伙们呆头呆脑,开始极不情愿,但好像被我们无形中牵到了鼻子一样,抵不住疼痛,磨磨蹭蹭,一步三停,才慢慢地爬进了玻璃瓶。
掏的过程中,我们不能用力过猛下重手,否则这些小家伙会被蕨棍弄伤或戳死。
如此,我们从东墙挖到西墙,从我家墙挖到他家,比赛着看谁挖得最多。最多的便是“蜂王”。能获此殊荣,让我们的虚荣心能得到暂时的满足。每天都能变换其主,今天你是大王,明天他是大王,大家都乐此不疲。
有时我们觉得还不过瘾,干脆跑到野外的油菜地里,去掏蜜蜂。
油菜地里真是蜜蜂的停机场,一架架小型“飞机”,从这朵花枝落到那朵花枝,不停地起飞降落,一派繁忙紧张的景象。
我们瞄准目标,屏息凝视,只用蕨棍轻轻一挑,花蕊上的蜜蜂笨手笨脚,四肢被磁铁吸住了一般,想逃也逃不掉,乖乖地踅进了玻璃瓶。
“哦,又挖了一只!”我们大呼小叫,向同伴炫耀显摆,庆贺自己的胜利。淘气、稚嫩的童声,比小鸟还快,窜进油菜的花海。
随后又不厌其烦,继续战斗,直到夕阳落山,光亮变暗,看到炊烟从烟囱里钻出来,顽童们远远听到父母亲唤儿的喊叫,才意犹未尽,踏在乡间的小路上,缓缓而归,留下小小的背影……
我们把折来的油菜花放进瓶里,油菜花是蜜蜂最好的陪伴。我们就像小时候的爱迪生,胸前捂着鸡蛋希冀孵出小鸡一样,我们也希冀蜜蜂有油菜花的喂养,能酿出蜜来。
晚上,有油菜花的香甜,有蜜蜂的忙碌,我们睡得酣畅,梦里氤氲着蜂蜜的甜蜜。
其实,过不了多久,瓶里的蜜蜂就奄奄一息了。没有尝到酿出来的蜜,我们多少有失望,有不甘。但第二天照样又去挖又去掏,并不能阻挡我们的热情。
整个春天,很快就过去了,我们并不悲伤。因为第二年春天,又如约而至。
春天,我们喜欢用玻璃瓶常常掏蜂儿,那里面装着童年的色彩,童年的快乐。
作者:朱小毛
热点图片
- 头条新闻
- 新闻推荐
最新专题

- 强国必先强教,强教必先强师。今年9月10日是我国第41个教师节,主题是“以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,谱写教育强国建设华章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