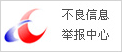满篓秋光茶油香
油锅“滋”的一声,我倒进母亲捎来的今年新榨的山茶油。香气升腾而起时,我仿佛看见她在晨光里缓缓直起身,望一眼拥群山入怀的万绿湖,又低下头,继续把枝头的油茶果一颗颗摘下。又是一年山茶油飘香的时节,窗外的风里,像是裹挟着一缕熟悉的香气,清冽而醇厚,像一根极细的丝线,不经意地,便将我的心从这片钢筋水泥的丛林,牵回了那万绿湖边的土砖灰瓦屋,牵回了那漫山遍野的山油茶香气里。
那土砖灰瓦屋,依偎在万绿湖臂弯里的龙溪村。那时的湖,还不叫万绿湖这个诗意的名字,我们都叫它新丰江。湖水是终年碧绿的,像一块巨大温润的翡翠,静静地卧在群山环抱之中。山是层林叠翠的,像一幅天然的水墨画,最挨近湖水的是墨绿,而后是翠绿,再往远处去,便成了含着烟岚的淡绿。而在那个秋高气爽的时节,最惹人注目的,却是那漫山遍野的古油茶树,山茶果由青转红,果皮微咧,油脂含量达到峰值,正是采摘最佳时机。然而春天的时候,山茶树不开艳丽的花,只是默默地将一朵朵象牙白的花藏在绿叶丛中,可它的果实却沉甸甸地压弯了秋天的枝头。
记忆里,采摘油茶果的时候天还未大亮,母亲便唤我起身与其做伴。上山的路上,露水很重,母亲总走在前面,她的解放鞋不一会儿就洇湿了。肩上挑着竹篓,竹篓里放着蛇皮袋,那篓子随着她的步子,有节奏地轻轻晃着,与扁担摩擦发出咿咿咿的声响。她的背影,在晨雾里显得格外清瘦,却又有着一种说不出的韧劲。山路两旁的草叶上,都缀满了晶莹的露珠,在微光里闪烁,我乐在其中。
母亲看见哪儿有果实累累的油茶树便钻进去,她的眼中溢出了油茶香。仿佛那香气,是绿色茶果壳略带青涩的苦味,是咧开棕色果仁里蕴藏着的油脂的芳香,是林间泥土与草木的气息,它们混合在一起,扑面而来,沁人心脾。母亲是采摘油茶果的好手。她的动作是那么娴熟,从不用蛮力去拉扯,只是用拇指和食指捏住那油茶果的根部,轻轻一拧,便听见“啪”的一声脆响,油茶果就干脆利落地掉进了竹篓。当阳光越过山脊,从高大松林的枝叶间筛下来,落在母亲因常年劳作而粗糙的手指上,那些光斑就在她摘油茶果的动作间跳跃成金色的弧线。
她偶尔会抬起头,用手肘上的衣服擦一擦额角的汗珠,望一望远处的万绿湖,眼神里便有了片刻的悠远;她也会絮絮叨叨地跟我叨起她小时候跟着外婆去摘油茶果的事,那些琐碎的旧话里,满是怀念——比如哪一年的油茶果结得最好,榨出的油是怎样个香法……这些絮叨,与林间的鸟鸣声、风声混作一体,听起来温柔而安详。那时的我,还不太懂得这些话语里的深情,只顾着在密集草丛里寻觅掉下来的软糯香甜的野柿子和椎栗。
不一会儿母亲的竹篓里的油茶果渐渐堆成了小山,红的、青的,沉甸甸地压着竹篓,也压着母亲眼角的笑意。她直起身,用粗糙的手掌轻轻拍了拍果堆,指尖划过果皮上的白霜,像抚摸着自家的孩子,嘴角弯出的弧度里,满是藏不住的满足——这是一年的收成,是罐子里清亮的油,是我们餐桌上的香。她让我扯开蛇皮袋口,把竹篓的山茶果倒进去。日头升到半空时,母亲把蛇皮袋口扎紧,牢牢系在扁担上,往肩上一放,顺手扶住两头的绳子,迈开步子便往山下走。我提着装有野柿子和椎栗的竹篓,跟着母亲下山,期待母亲回家把椎栗用柴火炒熟。山路依旧弯弯,她的腰弯得更沉了,解放鞋踩在落叶上发出的沙沙的声响,扁担与绳子的咿呀声,比来时更显厚重,却一步一步,走得稳稳当当。
如今,我离那湖,那山,那油茶树已是山一重水一程。城里的超市货架上摆着各式各样标签精美的茶油,可我总觉得,它们少了那一味草木与泥土的香——那是在晨露里浸润过的,被母亲的手指温柔抚摸过的,被万绿湖的清风吹拂过的魂……
油锅的滋响渐渐平息,茶油的香气却在鼻尖久久萦绕,不肯散去。这香气,从来都不是油的味道,是母亲晨雾里的背影,是万绿湖不变的碧色,是童年山径上的野柿甜与椎栗香,是母亲藏在岁月里,从未走远的温柔牵挂。
作者:黄贵美
热点图片
- 头条新闻
- 新闻推荐
最新专题

- 强国必先强教,强教必先强师。今年9月10日是我国第41个教师节,主题是“以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,谱写教育强国建设华章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