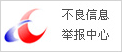老去的榨油坊
村东头那座榨油坊,如今只剩下一堵断墙了。
父亲第一次带我去榨油坊,是深秋的一个早晨。天还没亮透,他就把我从被窝里拽出来。我揉着眼睛,跟在父亲身后,手里提着装了二十斤茶籽的竹篮。村子里静悄悄的,只有我们的脚步声在石板路上“嗒嗒”地响。
榨油坊的门是厚重的杉木板,推开时发出“吱呀——”的呻吟,像老人伸懒腰的声音。屋里黑黢黢的,只有灶膛里的火光一跳一跳的。油坊主人陈伯正在炒茶籽,那口大铁锅斜斜地嵌在灶里,他挥动一把铁锹似的木铲,茶籽在锅里“沙沙”地响,冒出一股特别的香气。
“来了?”陈伯头也不抬,“先坐会儿,这锅快好了。”
父亲点点头,在门槛上坐下,掏出烟袋。我蹲在父亲旁边,看陈伯炒茶籽。火光映着他的脸,额头的汗珠亮晶晶的。
炒好的茶籽要碾碎。榨油坊的角落里,有一个巨大的石碾盘,直径有两米多。陈伯把茶籽铺在碾槽里,那头蒙着眼睛的老黄牛便开始绕着碾盘转圈。石磙“咕噜咕噜”地响,一圈,又一圈,不紧不慢。
碾碎的茶籽变成深褐色的粉末,散发着热腾腾的香气。陈伯用木铲把它们铲起来,倒进一个木甑里蒸。水汽“噗噗”地冒出来,蒸过的茶籽粉变得黏稠,颜色更深了。这时,陈伯取来十几个铁箍,铺上干净的稻草,把茶籽粉倒进去,包成一个个圆饼——这叫“油饼”。
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。榨油的家伙是一根巨大的樟木,中间掏空成槽,这就是“榨膛”。陈伯把油饼一个个竖着排进榨膛,插进木楔。然后,他走到屋梁下,那里悬着一根碗口粗的撞木,头部包着铁皮。
“嘿——哟!”陈伯大喝一声,抱起撞木,后退几步,猛地向前冲去。
“咚!”撞木重重地撞在木楔上。
整座榨油坊都震动起来,房梁上的灰尘簌簌落下。阳光从瓦缝里漏进来,照见无数细小的尘埃在空气中跳舞。
“嘿——哟!”
“咚!”
一下,又一下。木楔一寸一寸地往里走,榨膛里的油饼被挤压得“吱吱”作响。起初什么也没有,十几下后,第一滴油终于渗了出来,金黄金黄的,沿着榨膛底部的凹槽,缓缓流进陶瓮里。
接着,第二滴,第三滴……油滴连成了线,线汇成了细流。那油真是好看,澄澈透明,在陶瓮里泛着琥珀色的光。
父亲探身去看,脸上映着油光。他伸手蘸了一点,抹在我的手背上:“闻闻,这才是真东西。”
我把手背凑到鼻尖,那股香气直往心里钻。
第一道油榨完,陈伯会换一批木楔,再来第二道。二道油颜色深些,香气也浓些,父亲说这样的油炒菜最香。榨完油的饼叫“枯饼”,是上好的肥料,也用来药鱼——砸碎了撒在溪水里,鱼就会浮上来,但不是毒死的,只是晕一会儿。
那些年,我们榨过茶籽油、菜籽油,还榨过一次花生油。花生油最香,整条巷子都能闻到。榨花生油那天,陈伯破例给了我一把炒花生。
后来,村里通了电,有了机器榨油坊。机器榨得快,出油率高,但父亲总说,机器榨的油“没有魂”。他还是偶尔去陈伯那里,虽然要排队,虽然贵一些。再后来,陈伯老了,撞不动撞木了。他的儿子在城里开店,不肯回来接手。榨油坊就这样停了。
去年清明,我回老家,特意去看榨油坊。真的只剩一堵墙了。我站在那里,恍惚间又听见了“嘿——哟”的号子声,“咚”的撞击声,还有老黄牛拉着石碾“咕噜咕噜”转圈的声音。空气中似乎还飘着茶籽油特殊的香气。
父亲已经走了八年。如果他还活着,一定会站在这里,抽一袋烟,然后说:“你看,这才是真东西。”
风从断墙间穿过,狗尾草沙沙地响。我忽然明白了父亲的话——有些东西,之所以“真”,不是因为多么完美,而是因为它容得下时间,经得起一遍又一遍、笨拙的撞击。就像那座老去的榨油坊,虽然只剩一堵墙,但墙缝里渗出的,依然是岁月的油光,金黄,透亮,能照见一个人的童年,和一个时代的体温。
作者:罗铮
热点图片
- 头条新闻
- 新闻推荐
最新专题

- 强国必先强教,强教必先强师。今年9月10日是我国第41个教师节,主题是“以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,谱写教育强国建设华章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