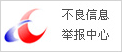唤一声“阿妹”
上午的日头亮堂堂的,顺着玻璃门钻进来,把货架上那几箱没拆封的饼干晒得暖乎乎的。我踮着脚搬芝士夹心饼干,一箱箱往高处货架塞。
门口突然传来一声:“阿妹,海盐饼干到了没有?”
我转头,看见小区的罗阿姐已经站在门口。她拎着菜篮子,几根葱叶从篮子缝里探出来,绿油油的。罗阿姐是老主顾了,常买完菜顺路进来看看。在她眼里,我虽是个守铺子的小老板,却更像是邻家妹子,没事总爱和我唠几句。
见我在搬零食,她赶紧三步并作两步过来,笑道:“阿妹,这么早就在忙?”这声“阿妹”脆生生的,热乎得像刚出锅的萝卜粄,烟火气直往鼻子里钻;这声“阿妹”,像是有根看不见的线,扯开我记忆的闸门。
小时候,奶奶也是这样叫我“阿妹”。老家天井里的日头,也是这样暖暖和和的,灶头柴火刚点燃,空气里就弥漫着一股松烟味儿,呛得人鼻子痒痒的。有一回,奶奶坐在灶台边的小板凳上,把刚蒸好的糕粄切成块。我在禾堂上追大黄狗,奶奶笑眯眯大声喊:“阿妹,慢点儿跑!过来吃块热糕粄!”这两个字灵得很,像奶奶唤鸡入笼的哨音,哨音一落,我就收了脚朝她奔去。
那时我不懂,以为“阿妹”就是个名儿,后来才明白,这不仅是个称呼,更是一个被捧在手心里怕化了的位置。奶奶的“阿妹”,是早上帮我梳头的木梳,齿子有点钝但梳得很轻;是吊篮里偷偷藏的熟鸡蛋,带着她手心的温度;是我跑远了回头看,总能看见她站在门口的影子。
奶奶走了好多年,老屋的炊烟早散了。我守着这家小零食铺,在城里过日子。原以为“阿妹”那一份暖早就跟着奶奶走远了,没想到,它藏在这市井的晨光里,被罗阿姐这样的街坊捡起来,又递给我。
在河源这座小城里,人和人之间的距离,有时候就是一声“阿妹”那么近。要是有个陌生的长辈笑着喊你“阿妹”,这冷冰冰的水泥楼好像都软和下来。不用血缘,就靠这两个字,客家人的热乎劲儿就出来了。像一杯温热的娘酒,把陌生人之间那点隔阂都化了。送货的大叔也好,晨练的阿婆也罢,喊一声“阿妹”,就是把你当自家孩子疼呢!有尊重,更有实打实的关心。
罗阿姐挑了几包苏打饼干,走的时候回头说:“阿妹,上午太阳要晒过来了,记得把门口帘子放下来啊!”我笑着答应,看着她拎着菜篮子汇进早市的人群里,葱叶还在晃。
中午回家吃饭,推开门,那份属于家的、更柔软的暖意便扑面而来。
儿子听见动静,从屋里“哒哒哒”地跑出来。刚睡醒午觉没多久,头发还翘着几撮,像只毛茸茸的小雀。他手里没拿玩具,倒是紧紧攥着半块威化饼干,嘴角、衣襟上沾满了星星点点的饼干屑,一头扑进我怀里。
我自然地蹲下身,搂住他暖烘烘的小身子,用指腹轻轻擦去他嘴角的渣子,又拍了拍他的后背:“阿妹,慢点儿吃,别噎着。走,妈妈带你喝水去。”
在我们客家人的心里,“阿妹”这两个字,是一声奇妙的呼唤。它无关性别,不分男女。在大人的眼里,儿子也好,女儿也罢,只要是心尖尖上的那块肉,便是她的“阿妹”。看着儿子被饼干糊成小花猫似的脸,满是依赖和快乐,我感叹道:原来爱是一个圆。
一声“阿妹”,从老屋斑驳的门槛,传到了我这间小小的、亮着灯的家;从奶奶那布满岁月纹路的、慈爱的嘴角,传到了我的唇边。它像一颗被时光精心保存的种子,一旦落入生活的土壤,便不管不顾地生根、发芽,开出一朵又一朵暖乎乎的花来。
窗外的天光渐渐柔和,孩子在客厅光晕里玩着积木,偶尔抬头冲我一笑。心里那片忙碌一天的尘埃,忽然就落定下来,满满的,都是安宁。
作者:朱秋萍
热点图片
- 头条新闻
- 新闻推荐
最新专题

- 昨日,中国建设银行·2025河源万绿湖马拉松在市体育馆鸣枪开跑,来自全国各地的万名选手齐聚“客家古邑”,用脚步感受城市脉动,为河源的山水人文增添了一道流动的风景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