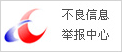藏在木箱里的清凉
南方的伏天像口密不透风的蒸笼,蝉鸣被热气泡得发黏,连穿堂风都带着股焦糊味。这时最盼的,是爷爷从阁楼搬下那只樟木箱,箱盖掀开的瞬间,仿佛能从闷热里劈开一道沁凉的缝。
那木箱是太爷爷传下来的,边角被岁月磨得圆润,红漆褪成了温润的琥珀色。每年入伏前,爷爷都会在箱底垫上三层旧报纸,再铺上晾干的艾草,然后将一摞粗布夏衣整整齐齐码进去。最神奇的是箱角那只青花瓷罐,里面总装着晒干的薄荷与金银花,揭开木塞时,清苦的香气能弥漫整个堂屋,像是给空气撒了把清凉的粉。
“来,试试这件。”爷爷从箱里翻出件月白色的对襟褂子,布料上还留着樟木的清香。我刚穿上身,就觉得后背凉丝丝的,像是贴了片浸过井水的荷叶。奶奶坐在竹椅上摇着蒲扇笑:“这是你爹小时候穿的,樟木箱养出来的布,越穿越凉快。”
木箱真正派上用场是在午后。日头最毒的时候,爷爷会把它搬到葡萄架下,掀开箱盖当小桌,摆上青瓷碗盛的酸梅汤。汤水表面浮着层碎冰,是清晨从井里吊上来的,碰着碗沿叮当作响。我趴在箱沿上喝,酸梅汤的酸甜混着樟木的清香,顺着喉咙滑下去,五脏六腑都像被浸在了凉水里。
有一回邻居家的小虎中暑了,脸蛋烧得通红,躺在竹床上哼哼。他娘急得团团转,爷爷听见动静,赶紧从木箱里翻出个蓝布包。包里是晒干的藿香叶,用擀面杖碾成碎末,冲上井水搅匀了给小虎灌下去。又从箱底抽出块靛蓝土布,在井水里浸透了,轻轻敷在小虎额头上。没过半个时辰,小虎就睁开眼喊渴,爷爷这才笑着把木箱里的酸梅汤分给他大半碗。
那年我十岁,趁大人午睡,偷偷把木箱拖到院子里“过家家”。学着爷爷的样子往箱里铺艾草,却不小心碰倒了装薄荷的瓷罐,碎末撒了满箱。
爷爷发现时没发火,只是蹲下来教我重新整理。他用竹篾扫帚扫去薄荷末,又从井里打了桶清水,把箱底擦得干干净净。“樟木最怕潮气,”他边擦边说,“但也不能暴晒,就像人过日子,得懂得藏着点清凉。”
立秋前要把夏衣收进阁楼,这是每年的大事。奶奶会把每件衣裳都抖三遍,再用樟木片裹起来,说是能防蛀虫。我踮着脚帮爷爷抬木箱,箱底蹭过门槛时,发出“咯吱”一声轻响,像是在跟夏天道别。爷爷说这声音是木箱在叹气,它也舍不得那些清凉的日子。
去年回老家,阁楼积了层薄灰,那只樟木箱还立在墙角。我掀开箱盖,艾草的香气混着樟木的醇厚扑面而来,恍惚间看见十岁的自己趴在箱沿喝酸梅汤,冰粒在碗底撞出细碎的响。奶奶从背后递来件新做的棉布衫:“你爷爷特意让我给你留的,说城里空调吹多了,还是老布穿着舒服。”
如今在空调房里待久了,总想起那只木箱。想起薄荷香漫过鼻尖的凉,想起棉布衫贴在后背的润,想起爷爷擦箱底时说的话。那些藏在木纹里的清凉,其实是岁月酿的蜜,无论过多少年,只要掀开记忆的箱盖,就能看见当年的月光,正顺着箱角的缝隙,静静淌成一条不化的星河。
作者:王瑶
热点图片
- 头条新闻
- 新闻推荐
最新专题

- 强国必先强教,强教必先强师。今年9月10日是我国第41个教师节,主题是“以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,谱写教育强国建设华章”。